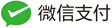《奧本海默》:突破傳記藩籬 雙重視角講故事
作者:王素芳
人物傳記片一向是電影中的高難度動作。一方面是這些著名人物的故事已經為大眾所知曉,將其影像化有很大壓力,另一方面極有可能因聚焦人物的豐功偉績而形成所謂的“英模片”“成就片”。近期,由克里斯托弗·諾蘭導演的《奧本海默》,聚焦于“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給人以很大的驚喜。影片采用多重手法進行表達,從而很好地解讀人物的心路歷程,引發人們去思考科學倫理精神。

《奧本海默》劇照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科學觀:科學倫理的自我審視
作為猶太裔物理學家,奧本海默對自己的國家有著深沉的愛,因此他應時代需求,矢志不渝地進行原子彈研發,并獲得成功,因此獲得“原子彈之父”的稱號。但是,《奧本海默》并沒有著眼于原子彈研究的全過程,而是定位于人物情感的變化,定位于對科學倫理的審視,從而使得整個影片充滿了人性的光環。
當戰爭處于膠著狀態時,奧本海默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原子彈的研究工作中,因為他意識到,只有發明原子彈來助力戰爭才能終結戰爭,因此認同自己的努力是科學的正義性。從這個角度看,《奧本海默》似乎是一部勵志片。導演選擇了具有深沉堅毅的藍眼睛的基里安·墨菲來出演片中的男主角。在組建原子彈研發團隊期間,奧本海默年僅38歲,他領導一群20多歲的年輕人,在沙漠上爭分奪秒,努力了兩年,最終獲得成功。影片中多次出現的集體跺腳聲,意味著不可抑制的群體狂熱,會把任何人送到任何無法想象的地方,奧本海默由此被推到很高的位置。
但是,在集體跺腳聲之外,更多的還是原子彈引爆之后痛苦的嚎哭、尖叫、焦尸、嘔吐等視聽元素的體現,這些幻覺讓奧本海默陷入深深的自我審視和反思之中。因此,坐在杜魯門面前的奧本海默,眼神黯淡,噙滿淚珠,內心復雜,他說:“我覺得我雙手沾滿鮮血。”“我們是否應該停止研究原子彈、關閉洛斯阿拉莫斯小鎮(奧本海默親手打造的軍工小鎮),免得與蘇聯形成軍備競賽。”杜魯門卻輕飄飄地回應:“你以為日本人知道誰發明了原子彈?他們只知道是美國,是杜魯門投的原子彈。”“既然蘇聯可能馬上造出原子彈,我們就更不應該關閉洛斯阿拉莫斯。”送走奧本海默后,杜魯門扭頭對助手說:“以后不要帶這個哭包來見我。”
原子彈最終沒有終結戰爭,而是讓人類處于被毀滅的邊緣。科學已經異化為政治機器上的一個籌碼,它的意義究竟有多大,這是《奧本海默》對科學倫理的深度審視。
時間軸:講好故事的雙重視角
作為人物傳記片,如果按照時間順序來講述人物的生平和際遇,無疑可以保證敘事鏈條的清晰性,但也可能墮入“爛片”行列,在長達三個小時的故事中,《奧本海默》的成功之處在于對時間軸的把握。
影片始于聽證會,終于聽證會,中間穿插奧本海默發明原子彈帶來的全民狂歡,以及戰后相關機構對他的構陷與指責,雙線交織,使得故事的講述始終以雙重視角展開,黑白兩種顏色交替呈現,充滿戲劇性的張力。
張力在斯特勞斯和奧本海默之間進行。斯特勞斯想進入內閣而舉辦參與人數更多、規格更高的“大聽證會”,這以黑白色調呈現;奧本海默被調查是否能繼續持有安全許可的“小聽證會”,以彩色畫面呈現,互為印證展開敘事。“小聽證會”是斯特勞斯因個人恩怨構陷奧本海默而私設的局,主題是調查奧本海默“對國家的忠誠度”——事關其是否還能繼續從事保密性質的科學研究和出入政壇。
斯特勞斯曾被奧本海默無意間調侃為低微的鞋販,同時他還懷疑奧本海默在愛因斯坦面前說他的“壞話”,因此將個人私怨演變成對奧本海默的政治報復。這對奧本海默的人生際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奧本海默》才能夠將科技與人性、科技與政治之間的反思達到相當的深度,從而突破一般意義上傳記片表現手法上的藩籬。
在時間軸的呈現上,即便是奧本海默本人身上,也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線性敘事,而是重點把握其內在心理動機的發展演變。奧本海默之所以投入精力去研發原子彈,是為了人類和平,這是一種愛國情懷。但是,原子彈引爆導致很多人死亡和流離失所,甚至推動美蘇軍事爭霸愈演愈烈,奧本海默陷入深深的反思,盡管后來他還因此陷入無窮無盡的人事構陷,并遭受了麥卡錫主義的種種迫害,但他坦然面對。這更是一種人間大愛。電影開篇的那句話,似是一語成讖:“普羅米修斯從眾神那里偷來火種送給人類,他自己卻被鎖在巖石之上遭受永恒的折磨。”當然,這或許是對英雄的最高禮贊,盡管諾蘭無意將奧本海默打造成完人。
藝術性:好看電影的內在邏輯
盡管《奧本海默》不是一部標準的文藝片,但是長達3小時的放映時間無疑對觀眾形成很大的考驗。諾蘭通過自己的藝術觀彰顯了自己的內在邏輯,那就是如何讓一個大眾相對熟悉的人物有更多的看點。
驚悚和懸疑或許是電影好看的必備要素。《奧本海默》始于聽證會,終于聽證會,無論聽證會的目的是想置奧本海默于死地,還是戰后的總統因政治的原因將其視為“棄子”,都讓觀眾感受到緊張刺激,為科學功勛者的命運深深擔憂。整個聽證會中,無論是證據還是證人都對奧本海默極為不利,似乎是“在劫難逃”,但最終的大反轉,讓觀眾長舒一口氣的同時,感到非常解氣。這不是中國式的“大團圓”,而是科學精神最終戰勝政治陰謀讓人產生的快意。
新穎的視聽手段是《奧本海默》抓住觀眾的又一個砝碼。因為“原子彈之父”的身份,觀眾或許對《奧本海默》的視覺奇觀充滿期待。但這種既有式的期待未必能夠給觀眾帶來真正的觀影體驗,因為事先會有各種各樣的想象。在《奧本海默》中,沒有大場面的視覺奇觀,更多的火光畫面的斷點式顯現,更讓人沉醉其中。與此同時,導演更多用視聽手段來彰顯人物內心的變化,使得人物更為立體客觀。
聲音的靜默和放大處理使得《奧本海默》深深地抓住觀眾。比如原子彈實驗引爆進行倒計時的時候,讓人心跳加快,引爆之后幾秒鐘的突然靜默,將奧本海默團隊幾年努力取得成功帶來的興奮推向高潮。多次出現的集體跺腳聲,一方面是對功勛英雄的肯定,另一方面何嘗不是命運對主人公的嘲弄?好看是電影的出發點,從《奧本海默》來看,多變諾蘭既有堅守也有創新。
(作者系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
隨便看看:
相關推薦:
網友評論:
推薦使用友言、多說、暢言(需備案后使用)等社會化評論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