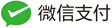一個腦袋兩個系統
3月27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認知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去世,享年90歲。
您沒有看錯――丹尼爾?卡尼曼是一位獲得了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他將心理學視角引入經濟學研究,行為經濟學由此奠基。
卡尼曼并不贊同傳統經濟學中對于“理性人”的假設,認為人的行為很多時候都是非理性的。他的核心思想和觀點,大多都凝練在了《思考,快與慢》這本書中。
書名《思考,快與慢》直白地道出了本書的主旨,即大腦的運行可以想象成兩個組成部分或者兩套系統的結合。卡尼曼參照心理學文獻術語,把這兩套系統分別命名為“系統1”和“系統2”,前者憑借直覺行事,速度較快;后者依靠反思行事,速度較慢。
“系統1”的運作根本不需要依靠我們平時常說的那種“思考”。比如,有一顆球朝你飛過來,你的身體會自然而然地躲開它,甚至在你的大腦反應過來之前。腦科學家認為,這個過程涉及了復雜的神經科學問題,它與人腦中最古老的一部分關系密切,并且貫穿于人類進化的全過程。畢竟,在原始社會,人類生活在充滿危險的復雜環境中。若是遇到一只老虎,停下來思考就是等死,管他三七二十一“先跑為敬”無疑更有助于生存。
“系統2”是反思式的。相比于“系統1”,它很懶惰,非必要不啟動;而且很低效,總得花點時間才能發揮作用。但毫無疑問的是,它精妙得多,能解決的問題也復雜得多。比如,如果有人問“411乘以317等于多少”,我們就會用到“系統2”;又比如,同樣是坐飛機時遇到強勁氣流,“系統1”會“說”,“飛機抖得厲害,嚇死寶寶了”,“系統2”會“反駁”,“墜機是極其罕見的,淡定!”這就是為什么在同樣的情境下,我們會看到有些人慌亂得厲害,有些人則冷靜得多。其中的關鍵在于,不同的人對于“系統1”與“系統2”的依賴程度不同。
“系統1”經常是無意識的,它依靠情感、記憶和經驗作出判斷,見聞廣博,但也很沖動,容易上當。有意識的“系統2”需要通過調動注意力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它雖然正確率更高,但需要“系統1”主動求教才能被“激活”。否則,它的反應通常都是靜靜躲在一邊,假裝自己不存在。
這也是卡尼曼并不認可經濟學中“理性人”假設的原因。在教科書里,“理性人”在做決策時總是會依賴“系統2”。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會依據“系統1”的指示行事,即便有充裕的時間也是如此。
要想讓“系統2”更好發揮作用,需要集中注意力。比如,在繁忙的火車站等朋友,若是刻意尋找,即使隔著一段距離你也很可能一眼看到他,即便你們已經很久沒見;但若一邊看小說一邊等待,大概率只能等著朋友找到你。
進一步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如果你將注意力分一點出來給別的事情,還可以勉強接受;但若將其過度分散到其他事情上,則很容易導致失敗。理解了這一點就能明白,為什么同時做好幾件費腦子的工作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就如同,絕大部分人都不能一邊在上下班高峰左轉駛入一條有很多行人的復雜線路,一邊心算“411乘以317等于多少”這道乘法題。
反過來說,如果人們足夠專注,就能屏蔽掉其他事情。在一本名為《看不見的大猩猩》的書中,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爾?西蒙斯兩位作者提供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證明。他們設計了一部兩隊傳籃球的短片,其中一隊穿的是白色球衣,另一隊穿的是黑色球衣。觀看短片的人需要數出白衣球隊的傳球次數,忽略掉另一隊傳的球。顯然,這個任務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短片播到一半時,一名套著大猩猩服裝的女性出現了,她穿過球場,捶著胸,然后繼續走動。這只“猩猩”出現了9秒鐘。最終的統計結果是,上萬人看了這部短片,但其中約有一半人并未注意到異常。可以想見,若是把專注這項“技能”運用到工作中,無論是嘈雜的辦公室還是吵鬧的鄰居,都不會對你產生任何影響。
卡尼曼另一個有趣的觀點是,“系統2”可以通過反復訓練,進化成“系統1”。大多數頂級運動員都是這一“進化論”的成功實踐者。頂級運動員經常會有令人驚嘆的表現,有時候是一腳匪夷所思的進球,有時候是一組超乎想象的躲閃。即便事后你問這些運動員“當時是怎么想的”,他們大概也只會回答“覺得就該這樣做”,如果他們夠坦誠的話。這就是“系統2”進化為“系統1”后的“條件反射”。換言之,任何人、任何工作,要達到卓越的程度,“練”就是了。寫稿寫不好,就沒完沒了地寫;打球打不好,就沒完沒了地打。總有一天,你的“系統2”會進化為“系統1”,技能變本能。(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肖瀚)
隨便看看:
相關推薦:
網友評論:
推薦使用友言、多說、暢言(需備案后使用)等社會化評論插件